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居民住进了高楼,邻里间很少交往和互动,甚至和住隔壁、对门的人家,没有任何交集,也是非常普遍的。毫无疑问,居住模式的改变,使中国传统城市社会中的那种紧密的邻里关系,正在一天天消失。
在中国城市中,“街”是人们共用的公共空间,经常与“邻”和“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词非常接近,有时相互重叠或紧密联系。它们都具有物质空间和抽象观念的内涵。它们都涉及到人们所居住的特定范围。
在中文辞典中,“街”的定义是“两边有房屋的道路”,与“街道”完全相同。由“街”构成了许多其他词汇,诸如“街坊”、“街市”、“街头”、“街头巷尾”等,在历史的语境中,其含义远远超出位置和空间,而经常体现居住这一区域的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街”一般是指一种物质性的空间,那么“邻”和“社”虽也具空间之含义,然则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邻”的通常定义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家”,并发展有“邻里”和“邻居”等词汇。
“社”有两个基本含义:在古代,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在今天,社是组织化的结构。前者的含义发展成为“社会”和“社区”。更准确的说,中文的“社区”则表示一个包括许多街道和邻里的区域以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正如《韦伯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对community定义中所说:即“那些享有同样权力、权利、或利益,居住在同一地区受同一法律和规章管束的人们”。总而言之,从街道、邻里到社区,是一个空间含义逐渐减少而文化含义逐渐增强的过程。
成都以及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过去便与西方有明显的差别。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其著名的《1400-1800年的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中的描述,在早期近代欧洲,像热亚那、巴黎、爱丁堡等城市都“朝着垂直方向扩张”,即在这些城市里,房屋总是尽量往天空伸展,多达五层、六层、八层乃至十层。而在过去的中国城市里,房屋多平行发展,一般一层或两层,人们的住家与街面经常只有一个门槛之隔,因此街头的商业活动很容易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他们的房子与街头接近,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常就发生在街头。成都居民的住所有公馆、陋室和铺面三种类型。公馆一般坐落在城北和城南,有围墙和门房,大多是富户和大家族居住,巴金的《家》便对这种公馆有细致的描述。有的大家族败落以后,公馆也被多个家庭共住,这种公馆多称“大杂院”。陋室散布全城各处,但大多集中在西城,为下层人们住所。
沿街的房屋称“铺面”,许多是底层作店铺,二层作住家。但铺面里亦有大量的一般住家户。他们不用走远便可到街头市场购物,甚至许多日用品跨出门槛在街檐下的货摊上便可得到。一位旅居成都多年的英国人徐维理(William Sewell)写道,每当晚上,在他所住的“小巷两旁已打烊关门的商铺前有许多小摊,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橙子和花生整齐地码成一堆,香烟可成双成单地卖”。
铺面则在每一街道的两旁,或为民居或出租给店铺,在东城商业区这种房屋多用作店铺。住在铺面人家的小孩,基本上就是在街面上长大的,那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所以成都方言里,在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甚至还被叫做“街娃(儿)”。
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在他们的门口和街边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他们有事找邻居,只要跨出门槛便可。不管是日常事务,还是紧急情况,他们都可以很快请到邻居帮忙。邻居之间一般的日常用品也可以借进借出。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们闲聊。在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方便进出,也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光线不足的内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开着,好奇的路人也可以瞥一眼屋里的风光。
这种状态基本维持到改革开放城市大拆迁之前。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小时候是住在单位大院里面,上小学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他几乎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特别是放学的时候,沿街一家一户,都觉得好奇,会停在门口,看别人家里的生活,几年下来,对沿街的每家每户情况,家里多少人,起居有什么规律,喜欢做什么饭,经济状况好不好,夫妻是否和谐......都了如指掌。
普通市民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由于缺乏官方控制,街头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生活条件差、休闲设施缺乏的人们,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等公共场所,可以找到廉价的娱乐。
在19世纪西方的工业城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舍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名著《公共人的衰落》中所说的:由于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的间隔,在那里“住在城里不同社区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在成都以及其他中国城市中,下层居民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密切,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
在邻里或街道上,人们彼此认识,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就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这些地方信息也易于传播。在过去的街坊,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喜忧,瞬间便可传遍整个街区。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居民们对小贩和工匠上门找生意并不感到烦恼。人们只需走几步就能到街头摊点、茶馆、小店和理发店,这些地方不仅提供日用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交往中心,人们在那里互通信息。晚清成都有六百多个茶馆,六百多个理发铺,加上街头巷尾,便是人们社交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好去处。
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们互相信任,相互帮助,一个院子共用的水井,就是人们便洗东西,边聊天的社交场所。如果家长有事出门,可以放心把小孩交给邻居看管;上班的人把经常把钥匙交给邻居,便于家人回来进门......他们和附近的劳工、小贩也很熟悉。小贩在门口卖东西吆喝,他们也不会感到厌烦。
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非常依赖挑水夫,由于井水含碱量比较高,不适合于饮用,市民饮用水必须从城外的河中取来,很多穷人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运水为生。茶铺、饭馆以及家庭都需要这种服务。在清末成都,上千这样的劳动者每天从河里挑水,外加四百多人从二千五百多口水井中取水,把饮水和用水送到人们家中。几乎每条街上都是他们挑水所洒下水迹和汗迹,人们可看到他们古铜色的流着汗水后背,有节奏地闪进千家万户。
这些水夫将这个行业的一些优良传统保留下来。成都的老人今天回忆起挑水夫仍充满感情和美好记忆。当代著名作家何满子,抗战时住在成都,他回忆到,挑水夫多不穿鞋,这并不是他们为省下鞋钱,而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使然,因为赤着脚,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
对大多数挑水夫来说,挑水不仅是谋生,而且是一条与邻里和社区联系的途径,比如帮助老人或有病灾的人家做杂务。一位老成都人写到,他认识的一个挑水夫负责华兴街一带几十个家庭,总计约百多人的用水。每挑来一桶水,他就在主人的大水缸上画一笔,五笔就是中文的“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桶水。到月底,每家的水费按“正”字的数量收缴。挑水夫和用户彼此信任,从来没有在支付问题上出现过混乱。
这种信任在成都很普通,在这里,邻居彼此认识并且几乎每天都要发生联系。传统的、邻里纽带紧密的社区中,人们生活在一个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彼此熟悉和平等的圈子里,人们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非常强烈。随着城市的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传统社区结构被彻底打破和消失;无处不在的钢筋水泥,阻隔了人们的直接交往。也这人们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吧。现在的中国城市,虽然“街”是必不可少,但是“街坊邻居”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个词将成为历史。
摘自《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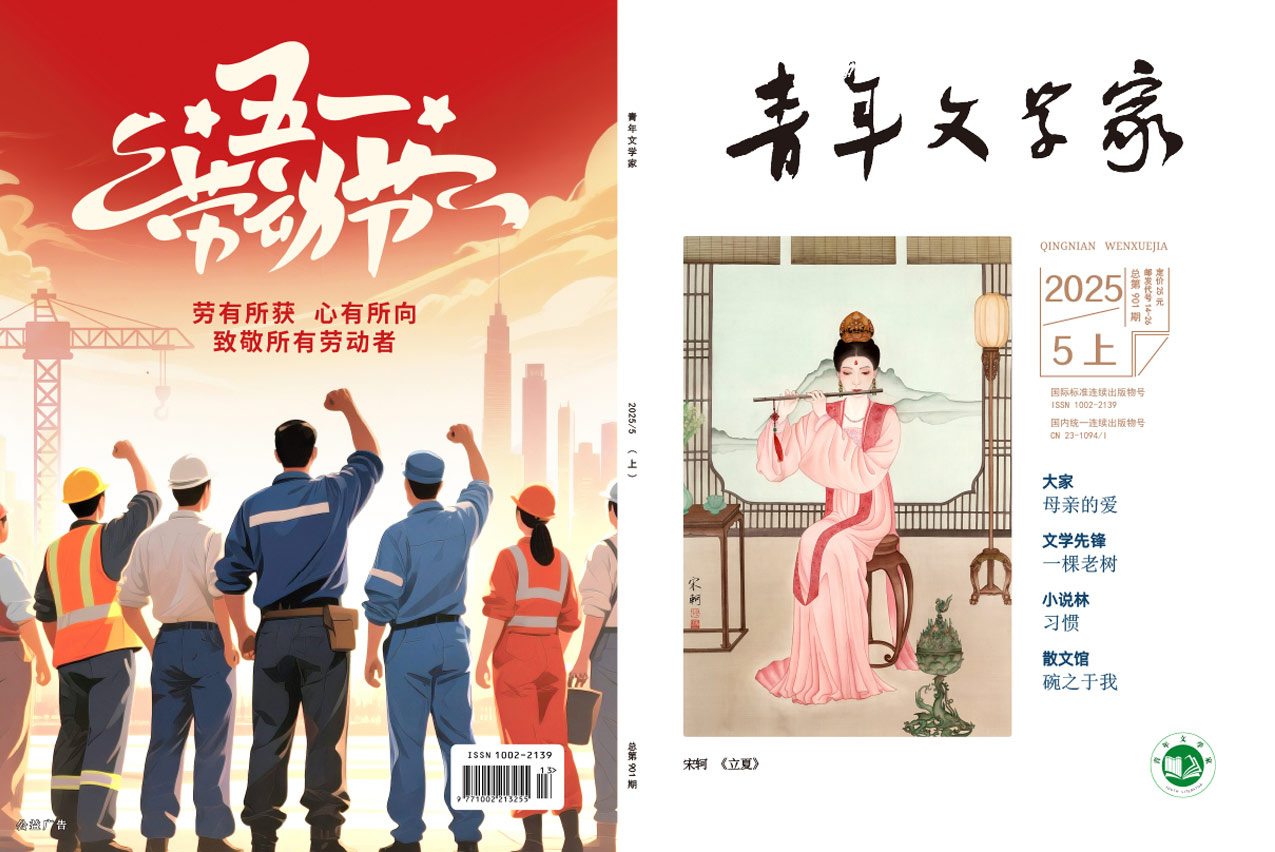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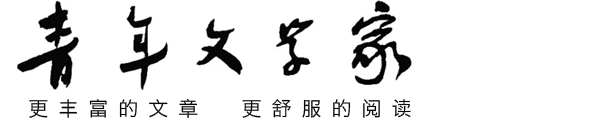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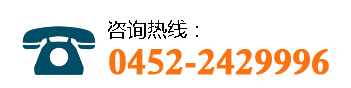
 关注微信公众号
关注微信公众号